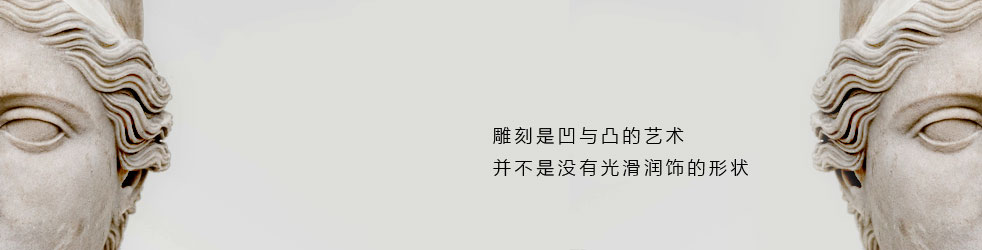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一、不似广东人
以前我尊称他为“伍老师”,拿了那张结婚纸后就慢慢叫他“老伍”了,又由于本土的关系,老伍成了“武汉的女婿”,为此他还调侃过一阵。因为在南方相传武汉人很利害,特别是生意人签合同时,很爽快,什么都答应,但履行合同时就不尽人意了。不知老伍是否对自己这张长期“合同”产生过疑虑呢? 初识老伍的有说他似印度人或印第安人的,就是不象广东人,他有一口还算流利的普通话,还吃得很辣。这是因为他从小在学院里长大,读中学所在的华南师范附中又是高才生与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所交朋友遍及各地却少有广东人等缘故,据他说,他在中山图书馆曾查到他们老家的伍氏族谱,说他们的祖上是从陕西那边随军南征过去的,是伍子胥的后人。 父母对儿女的婚事似乎比当事人更性急,而我当时则打着独身而不独居的主张,让父母伤透了脑筋,在传统观念上有不孝之嫌。记得身为党员的母亲曾单独找老伍谈过几次:听说你也是深圳的名人了,要注意影响......高级工程师的父亲更为含蓄:夏天不要开摩托车一起出去...女孩子穿的衣服少......。当初这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年龄又大、头发还长的广东人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女婿。日久见人心,想必现在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外乡人的诚信、踏实与能干。 他的父亲是典型的广东顺德人,是名厨师,从小教育他有礼貌,成为大院里小孩学习的榜样。母亲是个很义气的传统妇女,在文革的时候曾帮助过一些她认为没有问题的亲戚朋友,还与儿子成为对立派。老母亲不知道社会在飞速地转变,也不太明白自己的独生子是怎样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经过“血的洗礼”,上山下乡的再锻炼,革命理想的破灭,到重新上大学,改革开放,自我价值的重拾,他们这一代人背着沉重的时代烙印。所谓外乡人,身上有的是中国人的通性。 二、一生名艺 由于早年曾从事佛教寺院的壁画创作,走遍名山圣地,从而笃信佛教,还在九华山上入了个俗家弟子。河南登封的一位得道高僧赠给他四个字:“一生名艺”,并说他是一匹不羁的天马,一生将不停留地、无间断地飞奔。老僧的确说得很准,难怪上头有受益之人为他专门修了一条山路,让汽车能通到他修行的地方。 一方面老伍讲求一切随缘,心境平和,遇事不急燥,不强求,说起话来也慢条斯理,他认为急燥有碍智慧的发挥,大智慧者要衲于言而敏于行。另一方面他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各种可能性都敢于尝试,善于随时随地吸收周围环境中的精华为己用。也许他们这代人的时代使命感是与生俱来的,好象朝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奔跑才能获得快感,才能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那情形活象但丁描述的“人间炼狱”,非把人炼倒不可,但他们似乎越炼越精神,血气虽老,志气不衰。 年过半百的老伍此时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八面玲珑之心”。跟着他,所有的忙碌、疲惫皆习以为常,且转瞬即逝。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怀着孩子时,有一次挺着个大肚子到他办公室门口晃了一下,看见他在打电话给客户,就到其它办公室转一圈再回来时,他已谈完电话,边画着一张雕塑草稿,边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草草写给我的七八句诗:“一切都大了起来”,他说是刚才看见我之后写的,再一看桌上摊着好几张线描草图,还有两份合同传真件,这时电话又响起...,当时我在欣赏他的才智的同时恍然领悟: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运动,而运动的快感来自于这样点点滴滴的过程中。 三、人们看到的总是他的背影 后者当然只能看到前人的背影,但老伍也确实走得太超前了,有时让人觉得这未必是好事,当周围的人对他的行为有所反应、对他的观念表示认同支持或者在因打头阵而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后有所收获时,他又去打另一个头阵了。然而不是这样,老伍也就不是伍时雄,更不可能是“武汉的女婿”了。 伍时雄是国内最早运用摄影手段来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他的抽象摄影作品和理论将当时单调的摄影界带入了一个多元的分类介定的时代。当然他这个时期的成就与经历我是无缘分享的,也并非我所需要的,(还在读小学的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十几年后我会在他乡与这些作品和文章相遇,并为它们不被时代淹没的永恒性而感动),但后来旁人对他的记忆或多或少将他这段历史强加给了我,甚至走到美国的一个海岸,遇到两个在画画的同胞,谈起伍时雄这个名字时,就激动地告诉我:他当时可称为摄影界的南方一雄,他们在出国前经常读他的文章,订阅他创刊的《现代摄影》,因为那时很少有介绍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书籍杂志,早期《现代摄影》不仅在摄影艺术,而且在其它艺术领域里影响了一批人。 在人们看来他的事业日臻成熟时,传出他“下海”的消息,那个“下海”一词还带有贬义的年代,自然有许多同行朋友表示不理解甚至嘲讽,放弃即得的升职分房的机会,给自己的摄影事业划上一个句号,伍时雄的理由是要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表。就象在那场轰轰烈烈的“85思潮”艺术运动中,各艺术群体争名夺势时他曾预言“群体必将灭亡,艺术将走向个体”,他率先成为彻底的“个体工作者”,虽说两者在意义上有所区别。到他的“世纪末艺术工作室”在90年展览时,人们说在深圳这片“文化沙漠”上看到了绿洲。 作为一个艺术家,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是他们的天性,而能将这种天性发挥到他能触及到的各个领域的人实见不多。在艺术上,老伍将自己对立体空间和意念的独特思考运用在雕塑和陶艺作品中,追求作品本身永恒的艺术价值,而摒弃丝毫媚俗和商业的成份,保持了作品的纯粹和他自身人格的独立,这也正是他不惜付出代价换取的。同时老伍在出版业、平面设计、环艺设计和房地产、金融保险业、零售连锁店、旅游业、服务业等行业产品营销推广策划上都充分地发挥着综合性的能力,这是他区别于艺术家的个体魅力所在。人们也因而冠以他许多身份:从摄影家、雕塑家、陶艺家、收藏家到设计师、出品人、策划人,而这些角色他几乎能同时交替,“变”恰恰是他“不变”之法则,伍时雄就是伍时雄。他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作品可能就是他自己。 四、有了你走一大步 认识老伍若干年后,发觉他经常在朋友面前赞我,有句话最中听:以前自己只走了半步,有了她,我觉得可以走一大步。 我是在同学介绍下,到老伍的写字楼去求职时认识他的。因为我当时去南方,一心想找一份画廊的工作做,同学也误以为老伍的工作室是“画廊”,给了我一个不明确的地址,第一次找去时没找着,楼下保安告诉我:这里发廊有的是,却不见什么画廊。当我到他的公司找到他时已是第二年,他正在筹划出版《艺术市场》,而我正是他需要的帮手,但他还是要我等一个礼拜后听通知,后来他说是因为没见过女孩穿花裤子,要考虑考虑。我则真的等了一周,没去找其它工作,只因对他的印象实在很好。 与他相知是在工作中,合作创办《艺术收藏》,编辑《中国艺术收藏年鉴》,办展览,朋友们渐渐地拿我们的默契开玩笑了,初识的人说:你们长得真像,是他妹妹吗?反正象一家人。我们否认:两个异地人怎么会像呢!有一年为年鉴印一张贺年片,将两人的照片拼到一起,几乎拼成了一个人,连自己都很惊讶。 一直以来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们都以拍档、搭档相称,还笑言是广州美院的领导中央美院的,直到有一年,我们应邀去北京参加活动。闲余,老伍说想拍点长城的照片,我便带他去黄花城,那是我在89年时大学实习写生的地方,那里的长城保存完好,十分险峻壮观。因没能找到当年的村长和接待我们的老乡,我们决定在山上的峰火台里露宿。记得那天正好是秋分,一轮弯月当头,我们摘些野果充饥,将所有的衣服穿上,垫两块长城砖谈天说地,到后来我就不知不觉倒在他的怀里睡着了,在那狭窄的瞭望洞里,有冷嗖嗖的秋风呼哮,野松鼠偷吃着我们剩下的果子,而我睡得很熟,一觉醒来已是天高云淡...... 从相识、相知到相恋,走过风风雨雨的五年,到女儿两岁了,我还是不习惯称呼他为老公,其实我也很想对他说:有了你,在人生的路上我也走了一大步。 五、从容生活 有个好朋友是个女雕塑家,在生了儿子之后感慨:生活从此变得太具体了,一切似乎都落实到吃喝拉撒上。当然衣食住行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寻常百姓都是不可回避的,只是追求的质量不同罢了。 年青时老伍的衣服大多是他在香港电台的一位好友帮选的,从照片看当年的老伍还是很英俊潇洒的。现在因为我喜欢棉麻等自然质材的休闲服,所以他除了几件出席应酬的服饰外,基本上是简单的衣服,只不过款式和质地上稍讲究点,不过他穿起来走在街上还是众目睽睽的。 对于住所,我们当然最喜欢在顺德老家自己设计的那一栋,小楼面积不大,我只是在室内空间的设计上花了点功夫,力求住起来实用、舒适而不单调。整个房子是现代主义风格,摒弃繁锁和豪华的装饰,并结合了东方的庭院概念。但这房子最有价值的是周围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人文景观。我们常常在此乐不思蜀。 在行的方面,我们是最不讲究的。老伍开了辆无牌无证的“小绵羊”在深圳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达五年之久,交警一直没停地罚他,惹得记者朋友都想为此写专稿报道一下。该摩托废弃后,老伍拿它做了一件艺术作品。之后他经常独自步行、坐公车、有时借职员的自行车来骑,这样可以更多的接触生活中的人与事,就象他爱看电视新闻、资讯节目一样,他随时都有意识地吸收着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并有意识地利用时间煅练身体,看来他是不会去费功夫弄个汽车驾照的了。 六、钱财与富足是两个概念 钱财是靠数字来计算的,数字的大小则是相对而言,2比1大,3又比2大,那么多少为之大呢?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而富足则可以通过个人的感受来体验,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创造、沉思、艺术欣赏、爱情、亲情、友情所带来的满足与愉快,但许多人却忽略了这种感受,迷失在那可大可小的数字上。 我从来不认为老伍是有钱人,但他肯定是个很富有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体感受上,还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上,他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收藏现代艺术作品,拿理论家的话说是在“赞助历史”,到现在大大小小已经收藏近千件作品,以至于他筹划的私人美术馆失去预算,买了地就一直搁置在那里。曾有个画家对他说:“我的这幅画现在值6位数了!”,老伍说:“那又怎样,我可没打算拿它来换钱。”那为何收藏这些作品呢?他可不准备留给孩子,说是会害了后代,到头来可能会再还给社会。
发表评论
请登录